
育儿嫂在当下家庭中扮演的角色越发清晰了起来。社交平台上流传着“90后”“00后”高学历年轻女孩当住家保姆的vlog(视频日记),家政服务13825404095随着这些玩转社交网络的一代人的分享,让职业育儿看护在大众生活语境中变得更加受人关注。她们看起来具备专业知识、在家庭劳动中具备一定程度的职场技能,最重要的是,能够分担母亲的角色,给予儿童高质量的陪伴。
这些特征或许并非年轻一代专有,“赌王”的儿女们就多次公开分享自己由保姆们一手带大,其中舐犊情深、涌泉相报的部分往往引发讨论:母爱是可以被替代和外包的吗?若不是就职于显赫家庭,职业保姆的终身贡献是否也有对等回报?
有关母职意识形态的争论常常发生在“职场妈妈”与职业看护之间。麦克唐纳写:“她本来想要一场革命,却只能找到一个委内瑞拉人”,道出了这种探讨的两难。如今的社会框架下,存在更明晰、理想化,并且行之有效的答案——育儿的社会公共化,及其需要的政策福利和保障。在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亦有不同实践。
在《影子母亲》中,麦克唐纳关注“微观政治”,也即“权力在日常实践中传递的方式”,其实悬置了通过广泛的社会运动以争取更多权益的可能性。她着眼于“母亲”与那个“委内瑞拉人”之间的张力。谁在制造“影子母亲”?育儿嫂的处境是否完全对等于家庭主妇?卡梅隆·林·麦克唐纳在著作《影子母亲:保姆、换工与育儿中的微观政治》中探讨了这些问题。
密集母职的意识形态
母亲在儿童的早期发展阶段要永远在场、随时提供关怀回应,是“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核心。具体来说,自从19世纪时以父亲为中心的对下一代的教养转变成以母亲为中心,美国关于母职的论述就一直坚持孩子要由母亲来“全面照顾”。麦克唐纳谈到这样一种在科学性上乏善可陈的观念是如何变成“母职理想”,并固化了以家庭为核心单元的社会结构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关于儿童早期照料和青少年发展研究的第一期数据开始出现在媒体上。这一研究,尤其是媒体对该研究的“炒作”,对开创以科学指导育儿的新时代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母亲要成为0到3岁儿童最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恋对象(primary attachment),这种排他性的母子关系还要通过“高质量的陪伴”才能够建立,与之配套的,是“可完善的孩子”的假说。婴幼童的大脑在早期发展阶段能够变得更聪明、更有趣,这一假说给父母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提出了中产阶级文化理想中“好妈妈”角色的定义——如果你能培养出一个更好的孩子,就一定要这么做,成为孩子最佳的看护者。结果是,比对自己与育儿手册中的“理想母职”,妈妈们永远觉得自己的母爱未达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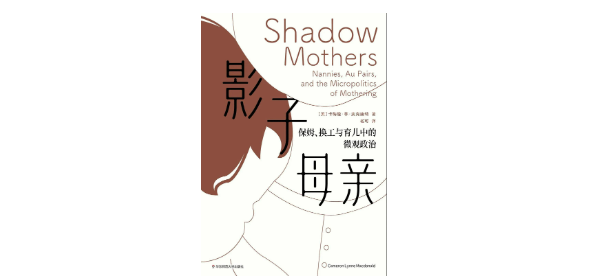
《影子母亲》,作者: [美]卡梅隆·林·麦克唐纳,译者:杨可,版本: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
二十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对新生儿行为的分析和洞察是为了打造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吗?对理论的正本清源没有那么难: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有关自我的问题,自我问题在心理学的夸大曲解中,变成了一种对个人主义的强烈渲染。其中最容易迈进的误区,就是将婴童想象成全然脆弱、被动的、等待照看的存在。迪迪埃·安齐厄在论述“自我-皮肤”精神外壳及其变型时,将母-子关系的二元反馈视作自我-皮肤的心理成因。在其对儿童专家贝里·布雷泽尔顿1973年制定的《新生儿行为评估表》的分析中,我们或许能够从婴儿的视角看到主体的内部历史,他们对“好父母”的内摄性认同与意识形态建制出的母亲的牺牲与照拂有很大不同。
母亲是最早的“他者”。梅莱妮·克莱因提出的“两种位态”理论,使母亲对于婴儿来说有了作为“好客体”和“坏客体”的分裂,无论母亲登录于哪一种位置,对婴儿需求的满足都不是一种施加于母亲身上的衡量标准,一个母亲会同时登录两种位置,这在帮助主体确立精神边界,通常在这一阶段结束后,孩子能够将母亲领悟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新生儿在母性环境中接受复合的、合适的照料的同时,也在对周围的环境发出信号,以期让照料更加精细化,同时探索物理的环境,寻找必要的刺激,以运用其潜能,激发感觉-运动的发展。婴儿是主动的,其与母亲的吸引和反馈回路是双向的,连续反馈则带来了内源性的控制力与心理驱动行为模型。布雷泽尔顿将这种框架概括为“母爱外壳(enveloppe de maternage)”与“控制外壳(enveloppe de control)”,前者由所有人与婴儿独立人格相适应的反应构成,后者由婴儿借此圈住周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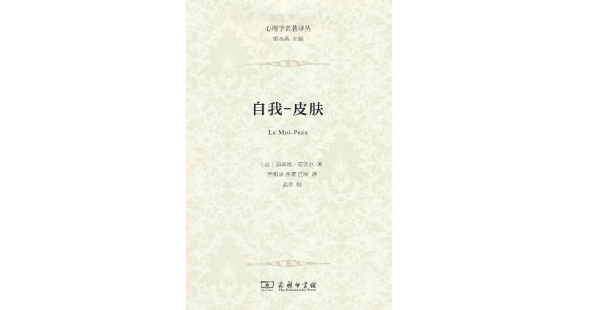
《自我-皮肤》,作者: [法]迪迪埃·安齐厄,译者:严和来/乔菁/江岭,版本:商务印书馆,2023年10月。
迪迪埃·安齐厄在这一阶段看到了新生儿这里存在着身体性前自我,集合了各种感觉和信息的冲动,具有遇见其他客体,对他们实施策略,并且与周围母性环境建立客体关系的特性。这一点其实证实了,人一旦出生,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的风格,且很可能有独一的自体感受。
实验心理学往往强调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对称性”,只有这种对称才能让母-子之间的关系趋向于一个稳定的系统。安齐厄则认为,只有平面(或轴线)才能得到对称。安齐厄的理论建立于他认为触觉和听觉、声觉一样,是我们最早的觉知。随着胎动、分娩时的挤压和摩擦;随着看护的触摸与离开,婴儿分别出“我”与“他”。触觉是双向同时发生的知觉,它使婴儿意识到那包裹着自我的“精神外壳”,在初始阶段,这外壳的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孩子,它为分离做好了准备。
“分界面”的提出,使我们得以看到,母亲与婴儿的关系不止是“刺激-反应”的模式,母亲与婴儿在这段关系里都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母亲的角色的重要性在被平面化成无微不至的看护者与爱的源泉之前,更深刻的是她与婴孩的双向关系。他们重新彼此确立自我,从而一定会从婴儿需求必不可少的代言人的位置上退位。外壳中包裹着自我的想象,发掘自我,我们要关注幻想及与之相关的无意识冲突,而不仅仅是母亲付出了多少。
谁在制造影子母亲
麦克唐纳提出“影子母亲”的概念的同时,进行了对阶级、种族问题的展演。虽然核心问题是母亲被视作社会再生产的唯一负责人,麦克唐纳对美国社会的研究使其无法放下对某一特定阶层的关注。瞄准中产阶层家庭的职业女性,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再分工是如何让母亲登录到“剥削者”的位置上的。
父权职场对个人提出一种预期:员工不必成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父权制下的阶层社会又对家庭提出一种要求:儿童要尽可能地继承文化与阶级资产;中产阶级职场妈妈的焦虑由此出现:如何通过中介实现阶层惯习与文化资源的代际传递?保姆、换工、看护很难被视作共享母职的伙伴,或婴儿周围母性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她们必须是“影子母亲”,执行母亲幻想中的育儿方式,在亲生母亲回家时自动消失,代替母亲为婴儿牺牲,密集母职理想要如同幽灵般附体在代理的身上,才能让妈妈们安心。

《母亲》剧照。
如果仅看见代理母职的商品化,与保姆们被物化,是远远不够的。麦克唐纳执着于从文化资源、经济阶级、种族待遇的差异中找寻“不公”,尽管承认女性劳动是一种无酬劳的、发生在私人领域的劳动,却无视了这种劳动性质的普遍性,仿佛全社会只有保姆这一特定人群拥有这种处境(或因为她们缺乏保障,在美国社会和经济价值结构中处于最低位,而将其视作浓缩了剥削压迫的阶层)。与此同时,她不乏趣味性地提出对育儿领域的一种见地,保姆们往往主张孩童的自然成长,而职业母亲们会倾向于参考指南资料“照本宣科”,这种二元对立显然不利于母亲们对专职儿童看护所执行的母爱代理的想象。
麦克唐纳很快遭遇了其中的矛盾之处,保姆们的代理角色除了分担了育儿中的杂活,也是一种情感劳动,比之工人的合理待遇,她们渴望情感上的认可,这种认可往往指向建立依恋——女性工作中最重要的回报。她们会与孩子们的亲生母亲开展“能力竞赛”,比谁能为孩子牺牲更多,这又导致了她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保障和待遇。麦克唐纳虽然创造性地提出竞争性母职的概念,却认为这种竞争源自母职的占有性与母性的脆弱,认为保姆与母亲同样是密集型母职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从而导致了谁对孩子来说是唯一的?谁是真妈妈?谁在做最有利于孩子的事?谁在享受高质量陪伴的时光?

《坡道上的家》剧照。
这一系列的争抢既看见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依旧着眼于“微观政治”,容易陷入“车轱辘话”的陷阱。母性的战场无法被转译成管理学的实践。比如将母亲对儿童护工、儿童成长的控制欲用服务行业的“三角”来理解,雇主-服务-顾客,由于服务总是发生在雇主/经理无法监管的地方,所以会采取岗位培训的形式,让服务尽可能“脚本化”,通过日志、汇报、突击检查来实施母爱监控。哪怕育儿学科用各种专家指南给予了监护人自信,育儿也依然不可能是一件脚本化的作业。原因正如上一部分所述,婴儿只要一出生就成为了独立的个体,拥有独一的自体感受,与母性环境生产独一无二的纽结。
面对社会分工的结果,要想打破僵局,就得让看护-母亲从二元对立的位置上下来,回归到她们共同的女性特质中。麦克唐纳提到了一种女性“反意识形态”,儿童游乐场,全职妈妈们在孩子们的社交空间交流、对照,获得社会世界的经验,发现“密集型母职”中对母爱不合常理的想象,比如少做了指南中要求的某件事对孩子也没什么影响,更认识到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的独一无二。职场妈妈似乎缺少了这一机遇,她们对制造一个“影子母亲”的迫切和焦虑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实在经验的缺乏。
女性普遍的辩证经验正是如此,我们所反抗的像失序一般的东西,我们自身也一直参与其中。
解得开的结
在对母亲-保姆的竞争关系的探讨里,孩子成长的控制权与归属权仿佛成了问题的中心,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不断被忽视,孩子究竟是否属于母亲?或者说,这个问题的提问者究竟是谁?
母亲真的会觉得一个孩子属于自己吗?波伏瓦批评弗洛伊德的“阴茎嫉羡”时提到,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种嫉妒,女人嫉恨的也不是男性逐猎的工具,而是他们的猎物。阴茎嫉羡是错误的,女性渴求的不是“有”的时刻,而是“是”的时刻。在实际经验里,孕育胎儿的过程往往喜忧参半,一方面孕妇落入了自然和物种的圈套,化作胶质的储备、孵化器、卵子……另一方面,在某个阶段,她是“生命”,是自为的存在,是具有固定价值的使人平和的幻想。女性并不是母亲。婴儿是独立的个体,母亲也是独立的女人,这组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主客体从母亲的身体内部就开始胶着。

《母亲》剧照。
正如实验心理学不理解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界面,父权建制中的母亲角色也用一种轴线或平面取代了母-子关系的复杂性。例如在“反堕胎”时声称胎儿不属于母亲,它是一个自主的存在,在赞美母性时却说,胎儿属于母体,不是消耗母体的寄生物。女性与胎儿之间的联结永恒地使男人恐惧,只有将其建构为一种属性脆弱的东西。
麦克唐纳眼中“解不开的结”正是此物。女人想象母亲对孩子来说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这种想象的内在性不是理所当然的,是被内化的。通过神圣化母职,女人们在“轮到”自己做母亲时,便占据了曾经的母亲的位置,但在完全实现这一女性命运的时刻,她依然是物种命运的附属品。女人并非在创作欲与自身的独特性中诞育了孩子,她是在身体的一般性中完成的孕育和分娩,新生儿不是母亲创作的作品。主客体正是在分离中绽出了独一性,而并非在依恋之中。
麦克唐纳的研究的最后一部分试图以经济管理学解开母亲与代理母亲之间的结:通过信任、自主权、双向沟通、共同决策来建立母职中的伙伴关系。在她的研究案例中,那些尊重保姆的专业技能、“共享”出母职,欣然接受自己不会是孩子生命中唯一提供母爱的角色的母亲们,建立起了健康、安全的依恋关系。这一答案似乎重新回归了理想化,试图弥合“为爱劳动”与“为钱劳动”之间的冲突。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其中的突破之处,对母职的探讨要突破意识形态的霸权。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劳动分工使职场妈妈走到了剥削者的位置,以密集母职意识形态来定制需求,不论这份需求是否真的对孩童有益。不论是母亲还是孩子,都无法从这个抑制结构中获益。而真正试图获益的,才是“影子母亲”的制造者。